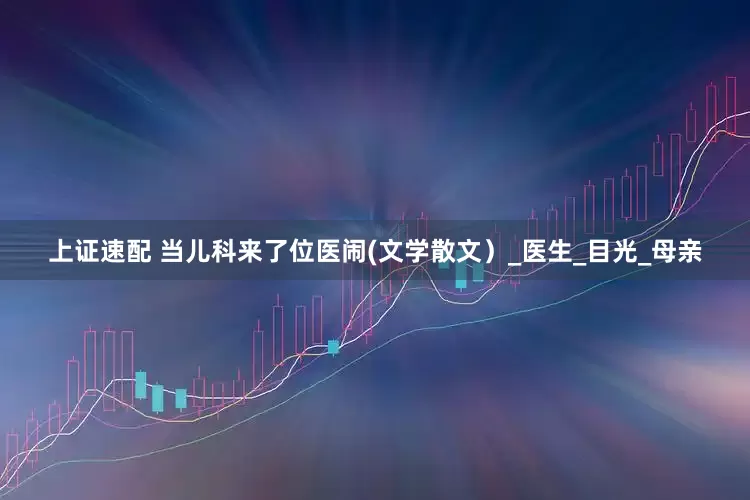
当“尽职好医生”的奖状才捧回家,掌声的余韵尚在耳畔缭绕,突然一块透凉的丝绸缎子贴上皮肤,横刺里就杀出一场医闹来,人生的讽刺,原是这样赤裸裸地呈现在你面前!
我是大城市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儿科医师,已在这方寸针尖之地耗了二十七载光阴。图什么呢?社区医院能有几个钱,不过是图那些婴孩的笑。婴孩的笑原是极短促的,偏在我心上烙出长久的印记,仿佛是对我人生的一点慈悲认证。日子原是镶着金边的,做着自己心尖上的事,阳光也仿佛对我格外慷慨些,哪知会发生事。
二零一八年的某一天,这层金箔便哗啦一声突然剥脱了,露出底下冰冷的铁板。此后漫漫长夜便是我的刑期,阖上眼,那女人的咒骂便如针尖般穿刺黑暗:“你停下!立刻停下你那双手!你站不得医生的位置,你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”。这声音仿佛捆住了我的魂灵,像是往静脉里注射了鸡血,此后,我竟像一个上了发条的木偶,在机械的动作下麻木不仁。
那日,本是替章医生的班。小甜甜,那个四月大的粉团子,被抱到我眼前。前囟门、耳后、口腔、心肺、胸腹……指尖循着规程一寸寸爬过,红球晃晃,分髋实验也循例做了。目光最后滑落到那小小的外阴处!只见白花花一层豆渣样的分泌物,糊住了下面。因为医院寒碜,没有设置儿童外阴分泌物检验这一项目,我便唤她母亲来看,叮嘱她回去要洗净,防的是粘连发炎。她倒是问得仔细,清水、禁用皂液、小纱布棉签……我一一交代得明白,像交代操控精密仪器一般嘱咐。
展开剩余75%诊室里别的孩子哭闹着,焦急的等在后头排着队。约莫半个钟点,门轰然洞开,一道人影裹挟着煞气直劈进来。一句刀子似的,兜着我的面掷下狠话:“你停下!立刻停下你那双手!你站不得医生的位置,你连做个人的资格都没有”。我觉得像是陡然被抽了骨,软在椅子上,眼前金星迸裂,半晌才看清——是小甜甜的母亲。她手指戟张,几乎差点戳进我眼球:“天诛地灭的事你都敢做!我女儿……她那地方被你生生撕裂了”
撕裂?这词烫得我耳膜生疼。那是妇科扩阴器下的噩梦,几时轮到一个儿科医生的寻常检视?满屋子病人和家属的目光瞬间粘上来,凝成一层无声的釉,将我烧制成一个待审的罪人。四下里静得能听见尘埃跌落的声音,没有一声辩解,没有一根救命稻草。
血涌上脸皮,我得为自己挣条活路。“同志”,嗓子眼发紧,“二十七年了,我从没出过这种岔子。小甜甜那,我可是半点都没沾!你信不过,咱们找地方验”。话音未落,一记耳光挟着风甩到我脸上,又脆又响,像枚银元砸在颊上。“医德败坏!黑心肝!你掰开她的腿太狠劲,撕裂了器官还想赖!担责!你必须担责!”
“刚刚为小甜甜分髋检查,本要化点力气,双腿要分开到一百八十度的,考虑到是小孩子,我没敢分那样大”,我挣扎着辩解。“只是底下全是白渣子,根本看不清颜色轮廓,哪来的撕裂出血”。 她不依不饶,一通电话让保姆把小甜甜抱了来,尿布一解——只见干干净净,尿布上半丝血痕也无。小娃娃反倒安稳得很,倒衬那母亲,像是自己被撕裂了。
我压低了声:“若真是当时撕出血来,孩子应该会嚎得惊天地泣鬼神,你能当场放过我,何必等到现在?那白花花的东西只是让你洗,你不是亲眼见过吗”?这时,医院分管领导赶来了,她却突然改口,说当时站偏了,没瞧见伤处,回去了才发现的。
一股腥甜堵在胸口,仿佛没有“一只眼睛”替我作证!领导竟也不将这位煞神请出,也不派人替我接下这烂摊子。门外候诊的队伍蜿蜒如蛇,我只得在那无数道目光的凌迟下,继续扮演我的儿科医生。那天的门诊?我好像踩在浮冰上,每一步都担着碎裂的恐惧。目光交错处,我如仓皇自闭的孩童,只想缩进壳里去。后来沈院长将他们引到隔壁的智力筛查室,那女人的咆哮仍是穿透薄墙:“派车!派人!全程盯着我们去我指定的医院!报销?谁稀罕!要紧的是处理这个医生!我要看你们怎么“处置”她!”
她那样急煎煎等着看我被“处置”,仿佛与我结了几世的血海深仇,恨不能将我枭首示众。满场的人,竟没有一个肯掷出一句公道话,只由得我在她的唾沫星子里沉浮。我的心也是肉做的啊!在这方寸诊室日日俯首,为社区的小苗苗们耗尽心血,何罪至此?天理何在?这世界,竟然如此荒唐?
午间向妇科张医生诉苦,她也惊诧:“视诊?哪能撕破?分明是讹上了”。末了又叹:“早知该叫上我辩一辩,如今你这一身脏水,别的病人眼里,你成什么了”!
后续是辗转听来的。僵持不下,院里派了个才满一年的见习医生陪着去了市里附属儿科医院。泌尿外科闭了门,只得挂了个急诊。急诊大夫看诊后说:“挺正常的,没事” 问及血迹,只道是轻微小阴唇粘连,因自然分离所致的一些小血丝,并非人为撕裂。
自此,我便如霜打的秋叶,整日浑噩。那年轻的见习医生怯怯寻到我:“周医生,那天可吓死我了!那家长冲进来,我真怕她当场打你!手抖得按不住,想报警都不敢……陪去医院路上也怕。后来,她让我带话给你:“以后检查轻点,半句歉意也无”!
医学院里的誓言,曾是多么庄严神圣的回响——健康所系,性命相托……如今听来,字字都像生了锈的铁钉,磨着耳膜。“当儿科来了位医闹”,能将一腔无名恶火,全部泼泻在一个医生身上,无需道歉,甚至带着一丝胜利的快意。我如何还能站在这里?背后同事的指指点点,如同无数根芒刺。每每忆起,那伤口就又深一寸。谁来慰我?若这样的“医闹”再来,我能否将那扇门对她关上?
二十七年的光阴,都织进了这件白大褂。委屈与辛酸,沉甸甸地织在里面,无人可诉。我的清白呢?谁来替我讨回?我的权益呢?谁来替我护卫?家中尚有牵绊,若有一日我被逼成疯魔,那身后的清白谁还我?这绝望原是虚的,浮于表面,但恐惧却是实的,沉甸甸交织在白大褂里。做一个儿科医生真不容易,我的心仿佛是一道彻骨的寒……
作者:步亚辉(民盟) 周静(农工党)
发布于:上海市众合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